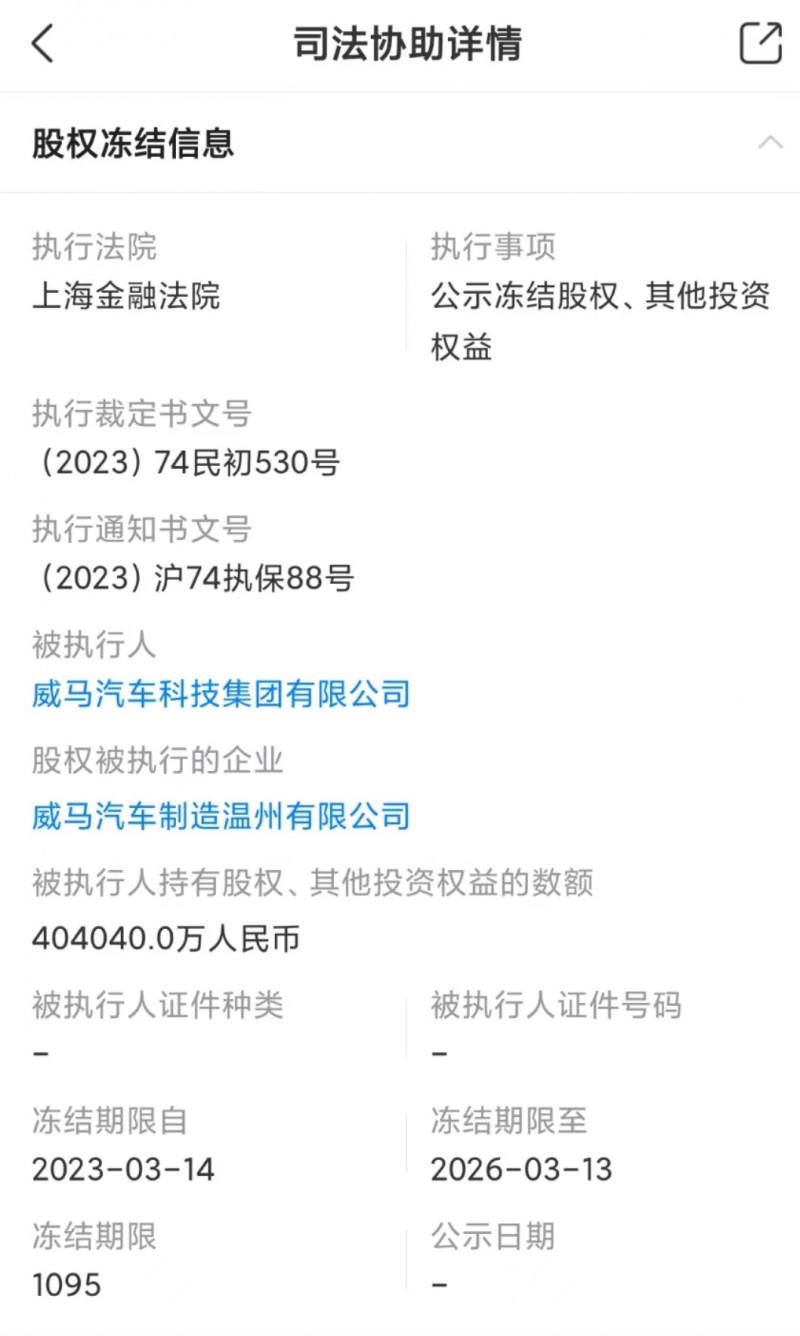清华教授胡左浩:中国制造未到生死攸关时刻
21世纪网在推出了“中国制造,这张面孔在流泪”的专题之后获得了巨大反响。目前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人力成本上升、两税并轨、人民币升值压力的“三座大山”,外资的相继撤离也在发出明显的信号——中国制造业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,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。
对此,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接受了21世纪网专访,他表示,目前我们的制造业正处于拐点之中,但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,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,我们有着广阔的农村市场,制造业转型将会呈现出多梯度与区域性的特点。胡左浩同时认为,未来的全球制造业将会多国家为中心的局面,二三十年内中国仍占有重要的份量。

清华大学教授胡左浩
从“微笑曲线”到“哭泣曲线”
“我们正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,但并未生死攸关”
21世纪网:您认为现在的中国制造业处于什么样的阶段?
胡左浩:目前来说,与发达国家相比,我们的制造业仍然有优势,但优势在变小。我们一直有制造业大国的背景,早年经济水平不高,资源和能力要先从制造业或者装配业做起来,各个方面也符合发展制造业的条件,比如土地成本低、税收低,基础设施成本低,当然,还有人工的工资低。国内的市场需求大,再加上成本的低廉,使前几年制造业发展比较快。
然而经济发展是阶段性的,中国经济经过20多年高速发展,不仅仅反映在总量的增加上,更反映在结构和质量的调整、社会发展和生活改善,可以说,我们目前处于制造业转型的拐点中。

21世纪网:可不可以说我们处在了转型的迫在眉睫时刻?
胡左浩:目前并未到生死攸关的时刻,离你说的“迫在眉睫”还差那么一点点。
什么叫生死攸关?日本在80年代碰到了这个情况:第一、日元大幅升值,出口产品价格升高;第二、日本人工资大幅增加,又受到中低端制造商的挑战,那时候真的是生死攸关了,只能靠不断的研发技术、争取海外市场来求生。
我们虽然也面临着人力成本增加和人民币升值压力,但不要忘记,中国的市场很大,梯度大,容量也大,这给很多企业提供了生存的空间。
我们高中低档次的产品都有需求,这是中国的收入结构决定的、城乡差距决定的,我们还有二三线城市、还有广阔的农村市场。
所以,在中国,说到制造业转型,是要分行业和地域的。比如沿海城市的玩具业和服装制造业等,现在苗头出来了,最难办的是广东那边中小厂子,地也贵、人工也贵,但也不是没有办法啊,富士康不就搬到河南去了吗?
21世纪网:您认为“生死攸关”什么时候才到?
胡左浩:十年左右。都说现在中国经济下行,但这是高位下行,总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高的,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市场的容量。
21世纪网:那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时间点导致了制造业的变化?
胡左浩:进入了2010年以后,制造业环境在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。一个是劳动力成本在增加,随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,人们对于工作和报酬的诉求也更高;
另一个是以往我们靠成本优势大规模生产,但是生产的产品同质化严重,导致市场竞争激烈,所以价格上不去,但是随着经济发展,成本又越来越高,利润大幅下滑,那么对我们众多企业提出要求,逼迫产业转型、技术提升和管理转型。
而从外部环境来讲,人民币面临着升值的压力,也是使得我们重新布局自己的制造业。
21世纪网:您提到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,其实现在最突出的表现就是“用工荒”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?
胡左浩:这得分两方面来看。一方面,用工荒确实是经济的长期隐患,这确实有新增劳动力供给大幅下降的原因,但其实在我看来,最核心的因素是劳动力素质提高了。原来劳动者都是小学、初中没毕业,脏累苦的活儿都愿意干;现在都是高中毕业,这些活儿还愿意干吗?
劳动大军早年发展靠压低工资、延长劳动时间这种外延式的增长,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增加,劳动大军工资提升是必然的要求,并且不可逆转,还有加快的迹象。这是对社会财富要合理分配的要求,不仅仅是经济问题,而是一个国家道德水平的体现,
另外,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消费、才能买房子或者旅游,劳动大军才是社会主体,只有他们工资提高了,整个社会文明才会进步。

中国制造
胡左浩认为,高铁跟飞机和汽车制造业比,主动权完全操控在中国自己的手上,而且慢慢打入国际。
«上一页 1 2 下一页»
 手机版|
手机版|

 二维码|
二维码|